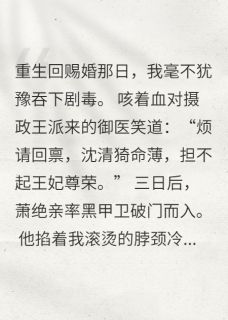重生回赐婚那日,我毫不犹豫吞下剧毒。咳着血对摄政王派来的御医笑道:“烦请回禀,
沈清猗命薄,担不起王妃尊荣。”三日后,萧绝亲率黑甲卫破门而入。
他掐着我滚烫的脖颈冷笑:“本王的地狱,缺个药引。”后来他毒发濒死时,
我涂着剧毒胭脂吻上他苍白的唇。
他却在我耳边嘶声呢喃:“冷宫那杯毒酒……是孤错了……”第一章:浴火重生,
开篇即地狱冷!刺骨的冷从骨头缝里钻出来。冷宫弥漫着陈腐的霉味,
混杂着绝望和死亡的气息。萧绝亲赐的毒酒,烧穿了她的喉咙,蚀烂了肺腑,
最后凝固在四肢百骸里,成了沉重的冰坨,拖着她向无边的黑暗坠落。沈清猗猛地睁开眼,
急促的喘息卡在喉咙里,变成一阵撕心裂肺的呛咳。肺腑间似乎还残留着那毒火烧灼的剧痛,
每一次吸气都带着血腥的铁锈味。
眼前不再是冷宫那漏风的破窗、剥落的墙皮和地上肮脏的草席。触目所及,
是熟悉的茜素红轻纱帐顶,绣着精致的缠枝莲纹。
空气里浮动着淡淡的、属于她闺阁的沉水香气息。阳光透过细密的窗格,
在地板上投下温暖的光斑,细小的尘埃在其中飞舞。“醒了?姑娘可算醒了!
”一个带着哭腔又满是惊喜的声音在床边响起。沈清猗僵硬地转动脖颈,
视线对上床边一张年轻圆润的脸——是她的贴身婢女,云袖。前世,云袖为了护她,
被萧绝下令活活杖毙在王府冰冷的石阶上。那张脸上此刻还带着未干的泪痕,眼睛红肿,
却满满都是失而复得的庆幸。“云袖……”沈清猗的喉咙干得发疼,
声音嘶哑得如同破旧的风箱。“姑娘,您可吓死奴婢了!您昏睡了大半天,怎么叫都不醒!
”云袖连忙倒了杯温水,小心翼翼地扶起她,将杯沿凑到她唇边,“快润润嗓子,太医说了,
您是受了惊吓,忧思过度……”温水滑过火烧火燎的喉咙,带来一丝短暂的舒缓,
却浇不灭沈清猗心头骤然腾起的冰冷火焰。不是梦!那蚀骨的恨意,那濒死的绝望,
那被彻底碾碎的尊严……清晰得如同烙印在灵魂深处!她回来了!回到了那万劫不复的开端!
“圣旨……”沈清猗猛地抓住云袖的手腕,指甲几乎要嵌进对方的皮肉里,
声音带着一种令人心悸的平静,“圣旨……是不是来了?
”云袖被她眼中的寒冰和手上的力道吓得一抖,杯中的水晃出来几滴。“姑娘?
”她怯怯地看着沈清猗苍白得没有一丝血色的脸,那双眼睛黑沉沉,深不见底,
翻涌着她从未见过的、令人胆寒的东西。云袖定了定神,
努力挤出一个安抚的笑容:“是……是来了。姑娘别急,是好事!天大的好事!陛下赐婚,
将您指给了摄政王殿下!圣旨是三日前到的,算着日子,再有三天,
就是您出阁的大喜日子了!阖府上下都高兴坏了,
夫人高兴得直掉泪呢……”云袖后面絮絮叨叨的喜悦之词,如同隔着一层厚重的冰壁,
模糊不清地灌入沈清猗耳中。唯有“摄政王”、“赐婚”、“三日”这几个词,
如同烧红的烙铁,狠狠地烫在她的灵魂上!三日后出嫁!三日后,
踏入那个金玉其外、实则比地狱更可怕的摄政王府!三日后,将沈家满门,将云袖,将自己,
彻底送入萧绝那个疯子精心编织的毁灭之网!滔天的恨意,冰冷刺骨,
瞬间冲垮了所有残余的迷茫和软弱。
绝望的眼神、云袖血肉模糊的身体、冷宫那杯鸩酒刺骨的腥甜……无数画面在脑中疯狂炸裂!
不!绝不重蹈覆辙!沈清猗猛地松开云袖的手腕,力气大得让云袖踉跄了一下。“云袖,
”她的声音异常平稳,甚至带上了一丝诡异的轻柔,如同淬了冰的刀刃,“去,
把西边耳房里,我那个带铜锁的红木小药箱拿来。立刻,马上!
”云袖被她突变的态度和语气惊得心头狂跳,那眼神里的东西让她本能地感到恐惧,“姑娘?
您要药箱做什么?您身子还虚着……”“去拿!”沈清猗的声音陡然拔高,
带着不容置疑的、斩钉截铁的威压。那不是一个闺阁少女该有的气势,
更像久居上位者不容忤逆的命令,带着尸山血海里淬炼出的煞气。云袖浑身一颤,
再不敢多问一个字,几乎是连滚爬爬地冲了出去。姑娘……好像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!很快,
那个半旧的红木小药箱被捧了进来。沈清猗眼神锐利如鹰,一把夺过。铜锁被粗暴地拧开。
箱内杂乱地放着一些普通的香粉、药膏、晒干的香草。她的手指精准地探入箱底,
抠开一个极其隐蔽的夹层暗格。暗格内,静静地躺着一个拇指大小的粗糙陶瓶。
瓶身没有任何标记,颜色灰扑扑的毫不起眼。沈清猗盯着它,眼中没有任何犹豫,
只有一片冰冷的疯狂。这是前世谢韫被流放前,偷偷塞给她的。他曾忧心忡忡地说过,
此物名为“寒髓引”,服之能立时引发酷似伤寒重症的脉象,高热咳血,凶险异常,
非万不得已绝不可用,对自身元气损耗极大。万不得已?还有比眼前更万不得已的境地吗?
她拔掉瓶塞,一股极其清苦、近乎辛辣的气息逸散出来。没有半分迟疑,沈清猗仰头,
将那瓶中仅存的一小撮灰白色粉末,尽数倒入口中!粉末入口即化,
一股难以言喻的、仿佛无数细小冰针攒刺的剧烈寒意瞬间从喉管直冲而下,
迅猛无比地席卷四肢百骸!五脏六腑像是被一只无形冰冷的巨手狠狠攥住、揉搓、撕裂!
“呃……”沈清猗猛地蜷缩起来,身体剧烈地颤抖,牙齿不受控制地咯咯作响。
刚才尚存的些许红润瞬间褪得一干二净,脸色变得比死人还要灰败青白,
冷汗如同溪流般瞬间浸透了单薄的寝衣,黏腻冰冷地贴在身上。“姑娘!姑娘您怎么了?!
”云袖魂飞魄散,扑上来想要扶住她。沈清猗猛地推开她,喉咙里发出嗬嗬的抽气声。
她挣扎着,用尽全身力气,狠狠地一口咬在自己的舌尖上!剧痛混合着药力带来的极致寒意,
让她眼前阵阵发黑,一股腥甜猛地冲上喉头。“噗——!”一大口暗红的、粘稠的鲜血,,
毫无预兆地喷溅在云袖素色的裙摆上,也染红了沈清猗身下雪白的锦被,
晕开一片刺目的、绝望的猩红!“啊——!”云袖吓得魂飞魄散,失声尖叫起来,“血!
来人啊!快来人啊!姑娘吐血了!救命啊——!”沈府瞬间陷入一片恐慌的混乱。
急促的脚步声、惊慌的呼喊声、杯盘落地的碎裂声……交织成一片绝望的背景音。
沈清猗的意识在剧痛和极寒的撕扯下浮浮沉沉。她能感觉到母亲撕心裂肺的哭喊,
父亲焦急沉重的叹息,府里乱作一团的脚步声。她像一具被遗弃在冰天雪地里的破布娃娃,
蜷缩在锦被中,每一次呼吸都带着灼痛和血腥味,每一次心跳都沉重得如同擂鼓,
撞击着即将碎裂的胸腔。不知过了多久,
一个带着明显宫廷腔调、略显苍老的声音在屏风外响起:“沈大人、沈夫人莫急,
老朽奉摄政王殿下钧旨,特来为沈**请脉。”王府的御医来了!萧绝果然不信!
沈清猗心中冷笑,冰冷的恨意支撑着她最后的神智。她猛地又是一阵剧烈呛咳,
身体痛苦地弓起,伴随着令人心胆俱裂的咳嗽声,
又是一小股暗红的血沫顺着苍白的嘴角蜿蜒流下,滴落在早已被染红的衣襟上。她眼神涣散,
如同风中残烛,气息微弱得几乎断绝。御医隔着纱帐望闻问切,又隔着丝帕搭脉良久。
传出的声音凝重无比:“沈**此症……来势汹汹,脉象沉迟细弱,如丝悬游,
此乃寒邪直中三阴,元气大伤之兆!凶险,着实凶险!恐……恐非吉兆啊!”“不!
我的猗儿!”沈母的哭声陡然拔高,绝望凄厉。屏风外一片死寂的压抑和悲鸣。
沈清猗在锦被下死死掐着自己的掌心,用那尖锐的疼痛提醒自己保持清醒,
保持这濒死的假象。她的嘴唇无声地翕动了一下,似乎想说什么,
却只发出一串微弱破碎的气音。云袖哭着伏低身子:“姑娘?您要说什么?
”沈清猗艰难地侧过脸,涣散的目光似乎想穿透屏风,看向那王府御医的方向。
“烦请……回禀……”她气若游丝,每一个字都像是从肺腑里硬生生挤出来,
带着血腥的泡沫,“沈清猗……命薄……福浅……担不起……王妃……尊荣……”话音未落,
她头一歪,彻底“昏死”过去,气息微弱得几乎难以察觉。御医沉默良久,
最终深深叹了口气,对着屏风外焦灼的沈父沈母道:“沈**病势危重,非人力所能及。
老朽……定当如实回禀王爷。”王府的御医走了,留下沈府一片愁云惨雾和深入骨髓的绝望。
时间被无限拉长,窗外日影的移动都显得无比缓慢。整整三天,
摄政王府那边再无任何消息传来。没有退婚的旨意,没有探病的慰问,
只有一片令人窒息的、风雨欲来的死寂。这死寂比任何喧嚣都更沉重,
沉沉地压在沈府每一个人的心头,也压在沈清猗绷紧到极限的神经上。黄昏时分。残阳如血,
泼洒在雕花的窗棂上,将房间映照得一片昏红,如同凝固的血浆。沈清猗半昏半醒地躺着,
高热和药力反复折磨着她的神智,身体虚脱得像一具空壳。
就在这令人窒息的寂静中——“轰——!!!”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,如同惊雷般炸开!
沈府那沉重的、象征着百年清贵门楣的朱漆大门,竟被人从外面用蛮力生生撞碎!木屑纷飞,
沉重的门板向内轰然倒塌,砸在地上,发出沉闷的巨响,扬起漫天灰尘!紧接着,
沉重、整齐、带着金属摩擦和撞击冰冷回响的脚步声,如同密集的鼓点,
踏碎了沈府最后的宁静,带着一股令人窒息的铁血杀伐之气,如潮水般汹涌灌入!“什么人?
放肆!”沈父惊怒交加的厉喝声从外院传来,
旋即被淹没在一片铠甲摩擦的铿锵声和冰冷刀剑出鞘的刺耳锐鸣中!
闺阁的门帘被一只骨节分明、戴着玄色冰玉扳指的手猛地掀开!力道之大,
珠帘被粗暴地扯断,玉珠噼里啪啦滚落一地!一道颀长挺拔、裹挟着无边寒意的身影,
如同地狱归来的魔神,踏着满地狼藉和夕阳的残血,一步跨了进来。
玄色金线蟠龙纹的亲王常服,在昏红的光线下流淌着冰冷的光泽,
衬得那张脸愈发俊美得不似凡人,却也冰冷得毫无生气。是萧绝!他身后,
是如同铁铸般沉默矗立的数名黑甲卫,冰冷的铁面具覆盖着脸庞,只露出毫无感情的双眼,
周身散发着浓烈的血腥与铁锈混合的煞气。他们如同冰冷的影子,瞬间占据了门口,
将内外隔绝,也将所有逃生的希望彻底碾碎。房间里的空气瞬间冻结了。
云袖和闻声赶来的几个小丫头吓得瘫软在地,牙齿打颤,连哭都哭不出来。萧绝的目光,
如同淬了冰的刀锋,缓缓扫过一片狼藉和惊恐的众人,最终定格在床榻之上。他一步一步,
不疾不徐地走来,靴底踩在碎裂的玉珠上,发出细微却令人心悸的碎裂声。那声音,
每一步都像是踏在沈清猗紧绷的神经上。他在床前三尺处站定。
夕阳的残光落在他轮廓分明的侧脸上,投下深邃的阴影。他微微垂下眼睑,
那双深不见底的黑眸,如同最幽暗的寒潭,毫无温度地锁住了沈清猗苍白如纸的脸庞。然后,
一只冰冷的手伸了过来。冰冷的指尖精准地按压在她剧烈搏动的颈动脉上!
“唔……”沈清猗再也无法抑制,身体猛地一颤,
喉咙里发出一声极压抑的、带着血腥气的呜咽。那冰冷的触感,
与前世记忆中他掐住她脖子时的力道如出一辙!深入骨髓的恐惧和刻骨的恨意如同两条毒蛇,
瞬间绞紧了她的心脏!胃里一阵翻江倒海,几乎要当场呕吐出来!她死死咬住牙关,
拼尽全力维持着昏迷的姿态,长长的睫毛如同垂死的蝶翼,在苍白的眼睑下剧烈地颤抖着。
萧绝感受着指尖下那异常紊乱、狂跳如擂鼓、却又带着一种奇异滚烫温度的脉搏。
他俊美无俦的脸上,没有任何表情,唯有那深邃的眼眸深处,
似乎掠过一丝极其细微、难以捉摸的幽光,快得如同错觉。薄唇缓缓勾起,那弧度冰冷刺骨,
没有丝毫暖意,只有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、仿佛在欣赏猎物垂死挣扎的玩味。他俯下身,
低沉磁性的嗓音如同情人间的耳语,却字字淬着寒冰,清晰地敲打在沈清猗的耳膜上,
也如同重锤砸在所有沈府之人的心上:“病?”“很好。”“本王有的是法子……‘治’。
”最后一个字落下,如同冰冷的判词。他直起身,目光扫过地上抖如筛糠的沈家众人,
声音陡然转厉,带着不容置疑的的威权:“来人!护送沈**——回王府‘静养’!
”冰冷的“护送”二字,如同枷锁落下。黑甲卫如同鬼魅般无声上前,动作粗暴地掀开锦被,
不容分说地将那具因药力和恐惧而虚软颤抖的身体架了起来。沈清猗的身体软绵绵地垂下,
如同被抽去了所有骨头的布偶,长发散乱地遮住了她瞬间惨白如金纸的脸,
也遮住了那双紧闭的眼眸深处,几乎要喷薄而出的、焚尽一切的恨毒之火。她被架着,
拖过满地狼藉,拖过父亲惊怒绝望的脸,拖过母亲撕心裂肺的哭喊,
拖过云袖瘫软在地的哀泣。夕阳的最后一点余晖,
被那扇破碎的、如同狰狞巨口的府门彻底吞噬。门外,摄政王府的玄色马车,
如同蛰伏的巨兽,静静地停在暮色四合的长街上,车辕上狰狞的青铜兽首门环,
在昏暗的光线下闪烁着冰冷幽暗的光。第二章:囚鸟为引,恨海生澜冰冷的玄铁窗棂,
将暮色割裂成一片片黯淡的囚笼。暖阁内陈设奢华,锦缎堆叠,金兽吐香,
却弥漫着比冷宫更刺骨的寒意。沈清猗被安置在宽大的紫檀木拔步床上,
像一件被随意丢弃的贵重物品。黑甲卫如同没有生命的铁像,无声地矗立在门外,
隔绝了所有声响,也隔绝了最后一丝来自外界的希望。高热褪去,只余下深入骨髓的不安。
每一次呼吸,空气里浮动的沉水香、龙涎香,都变得异常清晰。
更清晰的是身体深处那细微的变化——靠近门口黑甲卫身上散发的铁锈与血腥的冰冷气息时,
她会感到一阵莫名的烦躁;而当那沉重的、带着独特压迫感的脚步声自远而近,穿过庭院,
停在暖阁门外时……沈清猗的心脏会瞬间被一只无形的手狠狠攥紧,全身的血液仿佛逆流,
每一个毛孔都在无声尖叫着抗拒!门被无声推开。萧绝走了进来。
他已换下沾染尘土的亲王常服,一身玄色暗银云纹常服,更显身姿挺拔,
面容在跳跃的烛光下俊美得不似凡人,却也冰冷得毫无温度。他挥退了试图上前伺候的侍女,
偌大的暖阁只剩下他们两人。令人窒息的死寂。他走到床边,居高临下地俯视着她。那目光,
带着一种审视猎物的冷静和一种深不见底的探究,
一寸寸刮过她苍白的面颊、紧闭的双眼、微微颤抖的睫毛。沈清猗能感觉到那目光的重量,
冰冷而粘腻,如同毒蛇的信子舔舐过皮肤。她屏住呼吸,将自己伪装成一具无知无觉的空壳。
“沈清猗。”他开口,声音低沉,听不出喜怒,却带着一种掌控一切的漠然,“在本王面前,
装死无用。”沈清猗的指尖在锦被下深深掐入掌心,带来尖锐的痛感,
支撑着她最后一丝岌岌可危的镇定。她依旧闭着眼,一动不动。萧绝似乎轻笑了一声,
那笑声极短促,冰寒刺骨。他俯下身,带着薄茧的冰冷手指,再次精准地捏住了她的下颌,
强迫她抬起头,面对他!那双深潭般的黑眸被迫睁开,
里面翻滚着无法掩饰的、浓烈到极致的恨意和惊惧,如同濒死的困兽。她死死盯着他,
牙齿咬得咯咯作响,喉咙里发出压抑的嗬嗬声。“怕我?
”萧绝的拇指缓缓摩挲着她下颌冰冷的皮肤,力道带着一种狎昵的残忍,
眼神却如同淬毒的寒冰,“还是……恨我?”他的声音压得更低,
带着一种蛊惑般的危险气息,“本王很好奇,这份恨意,从何而来?”沈清猗猛地一颤,
巨大的恐惧瞬间压倒了恨意!他察觉到了?不!不可能!前世的一切他绝无可能知晓!
她猛地垂下眼睫,遮住眸中翻涌的情绪,身体因极致的恐惧和恨意的交织而剧烈颤抖起来,
挣扎着想要摆脱他的钳制。“放…开……”声音嘶哑破碎。萧绝非但没松手,
反而加重了力道,指节捏得她下颌骨生疼,仿佛下一刻就要碎裂!他凑得更近,
冰冷的呼吸几乎喷在她的耳廓:“本王的地狱,缺个伴。既然你命硬,那就好好活着,
活着……感受。”他猛地松开手,沈清猗脱力地跌回锦被中,剧烈地呛咳起来。萧绝直起身,
不再看她,仿佛刚才的逼问只是兴之所至的无聊游戏。他走到窗边,负手而立,
玄色的身影融入窗外沉沉的夜色,如同一尊冰冷的、俯瞰人间的神祇,
也如同一座无法逾越的囚笼。沈清猗蜷缩着,大口喘息,冷汗浸透了单薄的寝衣,
冰冷的黏腻感紧贴着皮肤。那深入骨髓的恐惧和恨意,如同两条毒蛇,
疯狂地撕咬着她的神经。萧绝……他就是个彻头彻尾的疯子!
一个毫无人性、掌控欲和破坏欲都达到极致的疯子!日子在极致的压抑中缓慢爬行。
沈清猗的身体在王府精心的“照料”下,表面的寒症渐消。但那奇异的体质却愈发明显,
她能清晰地感知到萧绝的存在,如同一个巨大的、散发着不祥气息的磁场。
他每一次踏入暖阁的范围,哪怕隔着重重门墙,她都会感到一阵心悸和莫名的烦躁。
更让她心惊的是,她的血液似乎带着一种连她自己都未曾察觉的安抚性的气息,
若有似无地萦绕在周身。这气息在萧绝靠近时,会变得格外清晰。恐惧如同冰冷的藤蔓,
缠绕上她的心脏。她隐隐猜到了什么,却不敢深想,只能将这荒谬的念头死死压下,
用更加厚重的冷漠将自己包裹。直到那个夜晚。子时刚过,万籁俱寂。摄政王府深处,
属于萧绝寝殿的方向,骤然爆发出一声如同濒死野兽般的、压抑到极致的嘶吼!
那声音充满了难以言喻的痛苦和暴戾,瞬间撕裂了夜的宁静!沈清猗猛地从昏沉中惊醒,
心脏狂跳不止。紧接着,是重物被狠狠砸碎的巨响!
瓷器、玉器、木器……各种碎裂声、倒塌声混杂着令人牙酸的碰撞声,
如同狂风暴雨般从寝殿方向席卷而来!间或夹杂着侍卫压抑的惊呼和急促的脚步声,
一片混乱!焚心!是焚心毒发作了!
前世模糊的记忆碎片瞬间涌入脑海——萧绝毒发时的狂态,如同地狱爬出的恶鬼,
周身数丈之内无人敢近!他曾生生撕碎过试图靠近安抚的侍妾!
沈清猗的身体不受控制地剧烈颤抖起来,寒意从脚底直冲头顶。她下意识地蜷缩进锦被深处,
捂住耳朵,试图将那可怕的声音隔绝在外。然而,那狂暴的声响如同附骨之蛆,穿透墙壁,
狠狠敲打在她的耳膜上,也敲打在她紧绷的神经上。每一次嘶吼,每一次碎裂,
都让她抖得更厉害。混乱持续了将近半个时辰,寝殿方向的声响渐渐低了下去,
只剩下一种令人心悸的死寂,仿佛暴风雨过后的废墟。沈清猗刚想松一口气,
暖阁的门却在下一秒被一股巨力猛地撞开!浓烈到令人作呕的血腥味和一种狂暴未散的戾气,
如同实质的潮水般汹涌灌入!两个黑甲卫,如同拖拽一件没有生命的物品,
粗暴地架着一个浑身浴血的身影冲了进来!是萧绝!他身上的玄色寝衣几乎被撕裂,
露出精壮却布满新旧疤痕的胸膛,此刻上面又添了几道深可见骨的抓痕,正汩汩冒着鲜血。
他脸色呈现出一种诡异的青灰,嘴唇乌紫,额角青筋暴起,如同虬结的毒蛇,
那双曾经冰冷深邃的黑眸,此刻赤红一片,充满了混乱、痛苦和毁天灭地的疯狂!
他像是刚从血池里捞出来,又像是刚从地狱最深处挣脱的凶兽,
喉咙里发出低沉的、意义不明的嗬嗬声,身体不受控制地剧烈痉挛着。黑甲卫显然也受了伤,
动作却依旧精准冷酷,径直将萧绝拖到沈清猗的床边,
然后毫不犹豫地将他沉重的、散发着浓烈血腥和煞气的身体,
狠狠地、直接地压在了沈清猗身上!“啊——!”沈清猗发出凄厉的尖叫!
前世被掠夺、被践踏、被赐死的所有恐惧和屈辱在这一刻轰然爆发!
她像一只被踩到尾巴的猫,爆发出惊人的力量,手脚并用,疯狂地踢打、抓挠、撕咬!
“滚开!萧绝!放开我!畜生!滚——!”她嘶声哭喊,
指甲在他手臂、脖颈上划出道道血痕,牙齿狠狠咬在他试图压制她的手腕上!
陷入半疯狂状态的萧绝似乎被她的剧烈反抗彻底激怒!他赤红的眼眸中凶光大盛,
喉咙里发出一声更加狂暴的低吼!一只沾满自己鲜血的大手猛地抬起,带着千钧之力,
如同铁钳般狠狠掐住了沈清猗纤细脆弱的脖颈!窒息!冰冷的死亡触感瞬间扼住了她的咽喉!
眼前的一切瞬间被黑暗吞噬,只剩下无边无际的绝望!不!她不能死!重活一世,仇未报,
家未护!她不能就这样死在这个疯子手里!生的本能和滔天的恨意混杂在一起,
爆发出最后的力量!沈清猗在极致的窒息中,双手胡乱地抓挠着,右手猛地挥起,
用尽全身力气,狠狠地挠向萧绝近在咫尺、因痛苦和暴怒而扭曲的脸!“刺啦——!
”指甲划过皮肉的声音清晰响起!萧绝脸颊靠近下颌处,瞬间被划开一道寸左右的血口!
两人温热的血珠交织涌出,有几滴甚至飞溅起来,
有几滴落在了他因剧痛而微微张开的的嘴唇上!时间仿佛在这一刻凝固了。
萧绝掐在她脖子上的手,力道猛地一滞!他那双被痛苦和疯狂彻底淹没的赤红眼眸,
在接触到那飞溅的血液时,如同被投入石子的深潭,
骤然泛起一丝极其微弱的、难以置信的涟漪!他下意识地,伸出舌尖,
舔舐了一下溅落在唇角的血珠。然后——奇迹发生了!
那双赤红眼眸中翻腾肆虐的、足以摧毁一切的痛苦风暴,如同遭遇了无形的堤坝,
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,奇异地、迅速地平息了下去!那暴起的青筋缓缓隐没,
乌紫的唇色也褪去了一丝令人心悸的死气。他掐在沈清猗脖子上的手,力道一点点松开,
最后完全卸去。他整个人都僵住了。压在沈清猗身上的重量依旧沉重,但他眼中的疯狂褪去,
只剩下一种极度的震惊和一种更深的、近乎贪婪的探究!
他死死地盯着身下因剧烈呛咳而蜷缩成一团、脸色青紫的沈清猗,那眼神,
如同在沙漠中濒死的旅人,突然发现了唯一的水源!沈清猗大口大口地喘着气,
喉咙火烧火燎,每一次吸气都带着血腥味和撕裂般的剧痛。她蜷缩着,
身体因恐惧和后怕而剧烈颤抖,泪水混合着冷汗糊了满脸。她透过模糊的视线,
对上萧绝那双褪去了疯狂、却变得更加幽深可怕、如同深渊般吸附着她的眼睛。那里面,
没有了杀意,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、炽热的、如同发现稀世珍宝般的占有欲!
“药……”萧绝的喉咙里发出沙哑破碎的音节,带着一种终于找到答案的笃定和狂喜。
他沾着血的手指,缓缓抚上沈清猗被掐出青紫指痕的脖颈,
动作带着一种令人战栗的、病态的温柔,却又充满了不容置疑的掌控,“本王的……药。
”这几个字,如同冰冷的判决,瞬间将沈清猗打入更深、更绝望的地狱!她浑身冰冷,
如坠冰窟!药引!她真的成了这个疯子的药引!这具重生后的身体,这该死的异变!
巨大的恐惧和屈辱如同海啸般将她淹没!她挣扎着想逃离这令人作呕的桎梏,
却被萧绝紧紧地禁锢在身下。他低下头,滚烫的、带着浓重血腥味的呼吸喷洒在她的颈侧,
贪婪地嗅闻着她身上因惊吓和挣扎而愈发清晰的那股奇异气息。
“呵……”一声低沉沙哑的笑从他喉咙深处溢出,
带着一种令人头皮发麻的满足和残忍的愉悦。
“沈清猗……你果然……是上天赐予本王的……良药。”从那一夜起,
沈清猗彻底跌入了炼狱的核心。“药引”的身份被粗暴地揭开,萧绝不再有任何掩饰。
他那原本就阴鸷反复的性情,在发现这唯一的“解药”后,
更是染上了一种令人胆寒的病态占有欲。“治疗”的手段,残忍而直接。有时是在深夜。
她被粗暴地从睡梦中拽起,萧绝披着寝衣,脸色在烛光下透着不正常的青白,
眼神却清醒得可怕,带着一种审视物品的冰冷。他执起她纤细的手腕,
冰凉的匕首锋刃轻轻一划——动作精准得如同在切割一件艺术品。鲜红的血珠瞬间涌出,
滴入早已准备好的白玉小碗中。他看着那鲜血汇聚,眼神专注而炽热,
仿佛在欣赏世间最美的琼浆。沈清猗痛得浑身痉挛,冷汗涔涔,却死死咬住嘴唇,
不让自己发出一丝示弱的**,只用那双淬了冰的眼眸,死死地、充满恨意地瞪着他。
有时是他“焚心”之毒隐隐发作,头痛欲裂,烦躁暴戾。他会如同鬼魅般出现在暖阁,
不顾她的挣扎反抗,强行将她拖入怀中,双臂如同铁箍般将她死死禁锢。
他将头埋在她的颈窝,滚烫的额头紧贴着她冰凉细腻的皮肤,
贪婪地汲取着那股能平息他体内地狱之火的奇异气息。他的呼吸沉重而灼热,
带着痛苦的低喘,喷洒在她敏感的肌肤上,引起她一阵阵生理性的战栗和恶心。
她开始变得沉默,极致的沉默。那双曾经会因恨意而燃烧的眸子,
渐渐沉淀为一片深不见底、毫无波澜的死寂寒潭。面对萧绝反复无常的索取,她不再反抗,
不再尖叫,甚至不再流露出明显的恨意。她只是顺从地伸出手腕,或者麻木地任他抱紧。
这种极致的顺从,反而像一根无形的刺,扎进了萧绝那深不见底的心湖。
他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烦躁和……失控。这女人,像一团冰。他用她的血缓解剧痛,
他抱着她汲取安宁,可她却越来越冷,越来越空。她眼底深处那片死寂的寒潭,
比任何激烈的恨意都更让他心头发堵,仿佛有什么重要的东西正在他眼前一点点流失、消逝。
这感觉陌生而危险,让他本能地抗拒。他开始变本加厉地试探她的底线。取血的次数增多,
禁锢她的时间延长。他会故意在她面前处置不听话的下属,鲜血溅落在冰冷的地砖上,
发出沉闷的声响。他冷眼观察着她,试图从那张平静无波的脸上找到一丝裂缝,一丝恐惧,
或者……别的什么。沈清猗只是垂着眼帘,长长的睫毛在苍白的脸上投下两片阴影,
如同精致的面具。她看着地上的血,眼神没有丝毫波动,仿佛在看一滩无关紧要的污水。
只有那微微收紧的、藏在袖中的手指,泄露着她内心翻腾的、几乎要焚毁一切的恨毒烈焰。
她必须活下去。为了复仇,她必须忍。这具身体是武器,也是枷锁。
她要利用这“药引”的身份,蛰伏,等待,积蓄力量,寻找那个能一击毙命的机会!机会,
在绝望的缝隙中悄然滋生。王府并非铁板一块。萧绝权势滔天,仇敌亦多如牛毛。
沈清猗被严密看守,但王府每年一度的“浴佛节”,摄政王需携“家眷”前往皇觉寺祈福,
这是维持表面尊荣的必要过场。对于沈清猗这个被强掳而来、身份尴尬的“王妃”,
这更是一个展示“恩宠”的绝佳表演。沈清猗知道,这是她唯一可能接触外界的机会。
她必须抓住。祈福那日,天气晴好。皇觉寺香火鼎盛,人潮涌动。
沈清猗穿着王妃规制的繁复礼服,华美却沉重。她脸上施了薄粉,掩盖了病态的苍白,
神情淡漠,如同一个精致的人偶,被萧绝牢牢牵在身边。萧绝一身亲王蟒袍,气度尊贵非凡,
脸上带着恰到好处的、疏离的温和,唯有那只握着她的手,力道大得惊人,如同冰冷的镣铐,